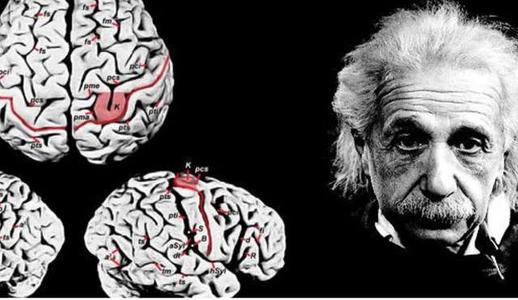
1955 年 4 月 18 日凌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位科学界的传奇人物,在普林斯顿医院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的离去,仿佛是一颗巨星从科学的天空陨落,全世界都沉浸在悲痛之中。然而,在这悲伤的氛围背后,一场关于他大脑的神秘故事悄然拉开帷幕。
当班的病理学医生托马斯・哈维,在对爱因斯坦的遗体进行解剖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 他偷走了爱因斯坦的大脑。爱因斯坦生前明确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大脑或身体被用于研究,更不想被敬奉起来,他希望火化后骨灰悄悄撒掉,不给狂热崇拜者留下念想。但哈维似乎被一种对科学未知的强烈渴望驱使,全然不顾爱因斯坦的意愿,私自将这颗被世人视为智慧象征的大脑据为己有。
“几天后,事情暴露时,哈维向爱因斯坦的儿子 —— 汉斯・阿尔伯特 —— 索要到了不情不愿但有追溯效力的允准,诉诸一条现今司空见惯的规定:一切调查完全服务于科学目的。” 布莱恩・伯勒尔在《谁动了爱因斯坦的大脑》一书中这样写道。但即便得到了汉斯・阿尔伯特勉强的同意,哈维的行为依然备受争议。很快,他便丢了在普林斯顿医院的工作。
失去工作的哈维,带着爱因斯坦的大脑来到了费城。在那里,他开始了一项看似疯狂的举动 —— 将这颗大脑切成了 240 块。他把每一块大脑都小心地保存在火棉胶里,火棉胶是纤维素的一种又硬又坚韧的形态,能够较好地保存大脑组织。随后,他将这些大脑碎片分放在两个罐子里,藏在了自家的地下室中。
本以为故事到此就已经足够离奇,然而,后续的发展却更加超乎想象。哈维的妻子对他保存爱因斯坦大脑的行为极为不满,甚至威胁要把这只脑子扔掉。在妻子的压力下,哈维不得不带着大脑踏上了辗转之路。他先是前往美国中西部,有一段时间,他在堪萨斯州威奇托市的一家生物检测实验室担任医务主管,在那里,他用苹果酒盒子把装有大脑的罐子藏在啤酒冷藏柜的下层,仿佛这颗大脑是他最珍贵又最见不得光的秘密。
之后,他又搬去了密苏苏里州威斯顿市,一边行医,一边利用空余时间尝试研究大脑。但不幸的是,由于没能通过为期 3 天的能力考试,他在 1988 年失去了医疗执照,人生陷入了低谷。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放弃对爱因斯坦大脑的执着。后来,他去了堪萨斯州劳伦斯市,在一家挤塑工厂从事装配线工作。在这段艰难的时光里,他搬进了加油站附近一栋二层公寓,命运的奇妙安排让他结识了邻居 ——“垮掉派” 诗人威廉・巴勒斯。两人经常相约在巴勒斯的门廊上喝酒,哈维有时会忍不住向巴勒斯说起大脑的故事,讲述自己如何把它切成小块寄给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而巴勒斯也会向来访者吹嘘:只要他想,就能拿到 “一小片” 爱因斯坦。
就这样,爱因斯坦的大脑在哈维的辗转迁徙中,度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岁月。直到 1985 年,哈维与加利福尼亚州的合作者们发表了第一篇有关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这颗沉睡多年的大脑才终于再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他们声称,在这只大脑中的两种细胞 —— 神经元和胶质细胞的比例异常。此后,又陆续有五篇论文发表,每一篇都报告了爱因斯坦大脑的单个细胞或特定结构上的其他异常表现。各研究背后的人员都满怀期待地表示,研究爱因斯坦大脑将帮助揭秘智力水平的神经基础。
然而,这些看似充满希望的研究,在佩斯大学心理学教授特伦斯・海恩斯眼中,却漏洞百出。几周前,海恩斯在美国认知神经科学年会上展示了一张海报,毫不留情地概述了上述六项研究每一项中存在的缺陷。
在 1985 年的原始报告中,哈维与合作者们发现,爱因斯坦大脑布罗德曼分区第 39 区,也就是颞叶、顶叶和枕叶交汇的区域,神经元与胶质细胞的比例显著小于对照组的 11 个大脑。但这个对照组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它们的主人年龄分布在 47 岁到 80 岁之间,年龄跨度极大,而爱因斯坦去世时为 76 岁,这样的对比缺乏科学性。此外,这些对照组的大脑都很新鲜,可爱因斯坦的大脑已经在地下室及啤酒冷藏柜里存放了三十年之久,大脑组织的状态差异巨大。更关键的是,细胞计数本身就是一项包含主观性的工作,而执行计数的研究人员清楚知道哪些组织来自爱因斯坦,哪些不是,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对结果产生主观影响。
1996 年,哈维同阿拉巴马科学家合作对爱因斯坦大脑的布罗德曼第 9 区,也就是前额叶皮层的一部分,以及其他五个对照组中的神经细胞进行了计数。该研究发现,各个大脑此区域的神经细胞数量及大小并无差异,不过爱因斯坦的脑部组织比对照组更薄。论文作者推测,更紧密的神经元意味着更小的细胞间信息传递差异,可能也意味着整体更快的处理速度。但这一系列推断实在有些牵强,正如海恩斯在海报中提到的那样,该结论仅仅基于爱因斯坦大脑中 1 平方毫米的小区域,样本量极小,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且,论文作者们还承认没有报告爱因斯坦大脑与对照组大脑的任何相似方面,这无疑让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1999 年,哈维与加拿大合作者们将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成果刊登到了全球最负盛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根据被切割前爱因斯坦大脑的照片,研究人员称,爱因斯坦大脑顶叶区域出现了部分折叠模式异常,而该区域一般被认为与数学能力有关。他们还报告说,爱因斯坦大脑顶叶区域比对照组宽 15%,而且更加对称。但与先前的研究一样,研究人员知道哪些照片才属于爱因斯坦的大脑,这就很难保证研究过程中没有主观偏向。并且,虽然作者们很快就把所谓的大脑差异与爱因斯坦的数学才能联系了起来,但海恩斯指出,爱因斯坦实际上并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大数学家,这样的关联缺乏足够的依据。
所有这些研究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们试图将单一人员构成的分组,也就是爱因斯坦这一个样本(该组的 N 为 1),与 “此人以外” 的人员构成的定义模糊的分组(该组的 N 大于 1)进行比较。当 N 为 1 的时候,要计算统计学差异几乎是不可能的,很难确定得出的结果到底是真实的差异,还是由于样本特殊性或研究方法的问题导致的侥幸情况。而且,就算得出了看似不错的统计学数据,要把人的技能及行为与大脑解剖学结果一一对应,也是一个几乎无法跨越的难题。我们根本没法知道,爱因斯坦大脑里的某个因素到底能否让他聪慧过人,还是说,它只不过是大脑里一个普通的、与智力无关的因素罢了。
回顾这些关于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我们不禁感到深深的遗憾。这些研究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财力,这些资金本可以用于更有前景、更有可能成功的科学研究工作。同时,也给爱因斯坦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他们基本上是被强迫同意参与这项爱因斯坦本人都已明确拒绝的研究。而且,多年来大众媒体对这些研究的报道,也误导了公众,让公众对研究结果和所谓的科学价值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爱因斯坦,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他的智慧和思想改变了整个世界。他深知公众对他的崇拜,也了解科学家们对研究他大脑的渴望。但他早就明白,试图通过研究大脑的神经元与胶质细胞、脑沟和脑回,来揭示天才的构成,很可能只是一场徒劳。据说爱因斯坦曾在普林斯顿办公室的黑板上写道:“并不是每一件计算出来的事,都有价值;也不是每一件有价值的事,都能够被算出来。” 这句充满哲理的话语,或许正是他对这些关于大脑研究的一种预见和感慨。
如今,爱因斯坦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他的大脑依然静静地躺在某个地方,那些被切成 240 块的大脑切片,仿佛在诉说着一段充满争议和谜团的科学往事。而我们,在不断探索大脑奥秘的道路上,是否也应该从这段故事中汲取一些教训,更加谨慎地对待科学研究,尊重每一个生命的意愿呢?